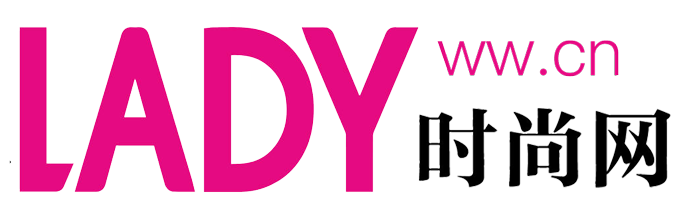又称黥刑、黥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对犯人的身体状况实际影响不大,但脸上的刺青会令犯人失去尊严。既是刻人肌肤的具体刑,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墨刑是奴隶制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
定义
古代的一种刑罚。在犯人脸上或额上刺字,然后再涂上墨。
秦汉时的英布就因为受过黥刑而被称为“黥布”。唐朝时的上官婉儿因为得罪武则天也被黥面,在额上留下刺青,刺青因为沾染了墨汁而无法清洗,使得原本面容姣好的上官婉儿变得丑陋不堪。后来,上官婉儿灵机一动,仿效刘宋寿阳公主的梅花妆,在额上刺字的地方以梅花形为装饰(一说为黥面时刺成梅花形),不仅毫不违和,还显得格外妩媚,后来,这种方法被其他女性模仿,并成为唐朝流行的化妆术之一。
在纹身的基础上,就发展出了墨刑,墨刑的特点一是继承了纹身时的疼痛感,二是有强迫性,三是带上了耻辱的痕迹。墨刑的产生时代也很早,早在尧舜时,三苗之君使用的五虐之刑,就包括黥面在内。《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爱始淫为劓、刖、椓、黥。"后传曰:"黥面。"又疏云:"黥面即墨刑也。"尧诛三苗,废"五虐",改用"象刑",就是给犯罪者穿上与常人不同得的衣服,以示惩罚,其中当受墨刑者要戴黑色的头巾。禹继尧舜之后开始使用肉刑,以后正式把墨刑定为五刑之一。
发展
最初,墨刑的施行方法是用刀刻人的皮肤,然后在刻痕上涂墨。《尚书·吕刑》篇中,"墨辟疑赦"一句后,孔安国传云"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周礼·司刑》一节中"墨罪五百"一句后,郑玄注云:"墨,黯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墨窒疮孔,令变色也。"这对墨刑的做法,已解释得十分详细,即先用刀刻面,再涂上墨,伤口结为疮疤,墨堵住了疮孔,就使皮肤变色。《礼记·文王世子》篇注云,墨型和劓、刖等刑一样,"皆以刀锯刺割人体也。"《国语·鲁语》也曾说:"小刑用钻凿,次刑用刀锯。"墨刑为小刑,当是使用钻或凿为刑具。其他各书述及墨刑时都是说用刀刻。这些说明,墨刑在最初规定为刑罚的时候,施行时用刀,而不是后世才采用的针刺。墨刑虽是轻刑,但人的面部神经极为敏感,用刀在上面刻刺,也是十分残酷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因为伤口感染而带来生命危险。
西周时,在墨刑之中还有(巾蔑)(黑屋)与黜(黑屋)的区别。(巾蔑)(黑屋)指在颧骨处刺刻涂墨,并在头上蒙黑巾,受刑者不仅失去奴隶主基层政权官吏的身份,而且成为罪奴。黜(黑屋)指仅刺刻涂墨,不蒙黑巾,受刑者只罢免职务,不成罪奴。西周刑法规定"墨罪五百",即列举应处以墨刑的罪状有五百条之多。《尚书·吕刑》篇亦云:"墨罚之属千。"可见,当时的刑罚是很严厉的,民众稍有小过黥面。据《周礼·掌戮》载,周代,奴隶主贵族常用黥面者作守门人,即"墨者使守门"。因为这些人的脸上带有耻辱的标记,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所以他们一般都不会逃跑。而且,黥面者的四肢都是健全的,不影响劳作。
春秋战国时,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各种苦役。战国时秦称墨刑为黥刑,秦国商鞅变法时,有一次太子犯法,不便加刑,商鞅便把太子的师傅公孙贾黥面,以示惩诫。公元前二一三年,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即刺面后罚作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当时,"黥京城旦"成为一项比较固定的处罚犯人的措施。这样的犯人遍布全国各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受过黥面之刑的囚徒。汉初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小罪被黥面。据《史记》载,黥布是六县人,姓英。秦朝时是个平民。少年时期,有位客人给他看相说:"将受刑以后封王。"到了壮年时期,因犯法,而受黥刑。黥布高兴地笑着说:"有人察看我的相貌说,受刑以后封王,就是这样吧!"听到他说这话的人,都滑稽地嘲笑他。黥布定罪后被送到骊山,骊山的刑徒有几十万人,黥布跟其中的头目、豪杰都有来往,终于率领那一班人逃到长江一带,成了一群盗贼。后来,英布归顺刘邦,汉初被封为淮南王。对此,《坚瓠集》"孙膑黥布"一篇中说:"淮南王黥布,姓英,黥非姓也。布尝坐洁黥.故人称曰黥布,黥乃墨刑在面之名,韵会以黥京为姓,误矣。"
汉初刑法沿袭秦制,仍使用黥面之刑。《汉书·刑法志》规定"墨罪五百",条款数目同周初一样。公元前一六七年,刘恒下诏废除肉刑,规定将当受黥面之刑者,男子改为剃去头发、颈上戴着铁制的刑具,去做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去做为期四年的捣米的苦役。此后直至汉末,黥面未再实行。但在汉代时,匈奴曾规定,汉朝的使节如果不以墨黥面,不得进入他们的单于所居住的穹庐。有一次,王乌充任汉朝使节,出使匈奴时就顺从了他们的规矩,单于大喜,同意让匈奴的太子到汉朝作人质,请求与汉和亲。有人说,匈奴的这种规定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只是用墨画在脸上,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并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这事实上是原始纹身习俗的一种变异。
汉代以后,随着某些肉刑的恢复,黥面也重新被采用。据《酉阳杂俎》载,晋代规定,奴婢如果逃亡,抓回来之后要黥其两眼上方,并加铜青色;如果第二次逃跑,再黥两颊;第三次逃跑,黥两眼下方。上述三处,施行时都要使黥长一寸五分,宽五分。
记载
《酉阳杂俎》中还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证明黥痕可以深深印到人的骨头上。唐代贞元年间,段成式的从兄经过一个叫黄坑的地方,他的随从拾取死人的头颅骨,打算用它配药,看见一片骨头上有"逃走奴"三个字的痕迹,色如淡墨。段成式判断这是古时被黥面的人的头骨,而且很可能就是晋代逃亡过的奴婢的遗骨。
据《南史·宋明帝纪》,四六八年,宋刘彧颁行黥刑和刖刑的条律,规定对犯有劫窃官仗、伤害吏人等罪者,要依旧制论斩;若遇赦令,改为在犯人两颊黥上"劫"字,同时割断两脚筋,发配边远军州;若是五人以下结伙以暴力夺取他人财物者,也同样处罚。另据《隋史·刑法志》载,五○二年,梁武帝萧衍又颁定黥面之刑。黥面的施行方法,大概不是用刀刻,而是用针刺。如果犯有抢劫罪应当斩首而遇赦者,要黥面为"劫"字。这种刑罚实行的时间不长,五一五年即予以废除。
五代后晋石敬瑭滥用峻刑酷法,恢复黥刑,改称刺字,并与流刑结合使用,称为刺配,沿用至清。
北宋时,黥面之刑一律改用针刺,因而又称为黥刺。对此,《宋史·刑法志》中有明确记载。北宋时还规定,犯人的罪状不同,刺的位置及所刺的字样排列的形状也有区别。凡是盗窃罪,要刺在耳朵后面;徒罪和流罪要刺在面颊上或额角,所刺的安排列成一个方块;若为杖罪,所刺的字排列为圆形,三犯杖刑移于面,径不过五分。
凡是犯有重罪必须发配远恶军州的牢城营者,都要黥面,当时称为刺配。北宋名臣狄青年轻时也曾被刺配,后来显贵,仍保留着刺的印记,不愿除掉它。直到南宋时,刺配的做法都是很常见的。
辽代刑法也有黥刺,和北宋的施行方法相同。据《辽史·刑法志》载,辽代墨刑也是用针刺,但刺的位置不完全一样。一○三三年,辽兴宗耶律宗真规定,对判为徒刑的犯人,要刺在颈部。奴婢私自逃走被抓回,如果他(她)同时盗窃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不得黥刺其面,要刺在他(她)的颈或臂上。犯有盗窃罪的,第一次犯刺右臂,第二次犯刺左臂,第三次犯刺脖颈的右侧,第四次犯刺脖颈的左侧,如果第五次再犯,就要处死。辽代其他刑罚非常残酷,唯独黥面之刑比前代要宽大一些。
《金支·刑法志》称金代规定犯有盗窃罪且赃物在十贯以上五十贯以下者要处以徒刑,同时刺字于面部,赃物在五十贯以上者要处死。元代仿照宋、金的有关法律,对盗窃罪要予以刺字,并同时施加杖刑,刺的方法和仗的数目有非常详细的条款。《元典章·刑部·强窃盗》则规定,汉人、南人犯盗窃罪者,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颈项,蒙古人有犯不刺。另外,对什么情况下免刺、什么情况下已经刺过仍要补刺等等,也都有具体的规定。
明代关于黥刑的法律,与宋元大同小异,但使用的范围更狭窄一些。明初朱元璋于一三九七年五月在御制《大明律序》中规定,"除党逆家属"外"俱不黥刺",即谋反叛逆者的家属及某些必须刺字的犯人予以刺字,其他各类犯人一律不再用宋代那种刺配的方法。另外,对于盗窃犯,初犯者要在右小臂上刺"窃盗"二字,再犯者刺左小臂,第三次犯者要处以绞刑,对于白昼抢劫他人财物者,要在右小臂上刺"抢夺"二字,如果再犯抢夺罪者,照例在右小臂上重刺。情节比较轻微的偷摸都勿须刺字。明代的法律中对免刺、补刺的规定也有明确的条文。
清代的黥刑主要施用于奴婢逃跑,而且常和鞭刑并用,称为鞭刺。
据《大清金典》载,一六五四年,朝廷议准,对于逃亡的奴婢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要免予鞭刺。一六五六年又规定,犯盗窃罪者也要刺字。一六六五年规定,对逃亡的奴婢的刺字不再刺在面部,和盗窃罪一样都刺小臂。第二年又下令说,如果逃亡者改刺小臂,这样逃亡者越来越多,无法稽查,因此仍旧改为刺面。一六七三年诏令,凡是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逃亡者要免予鞭刺,如果是夫带妻逃、或父带女逃、或子带母逃者,妇女免予鞭刺,如果是妇女单独逃亡者不能免除。这样的规定,说明清代奴婢的处境悲惨,而且逃亡现象严重,同时说明统治者对逃亡者的镇压也非常严厉。并且,清代法定满人轻囚不刺,重囚刺臂,汉人一律刺面。刺臂在腕之上,肘之下;刺面在鬓之下,颊之上,大小一寸五分见方,面阔一分半。罪名与发配地点分刺在左右两颊。清代狱吏以刺字代替公文,常有公文应改而所刺墨字无法涂改的情况出现。清末法制改革,始将刺字废止。纵观各代实行黥刑的历史,古时刀刻法的黥面变为宋、元、明、清的刺字,虽然残酷的程度是在逐渐减弱,但是对受刑者的人格污辱则丝毫未变。
墨刑,又名黥刑,黵刑,刺字,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肉刑,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修订《大清律例》时才被彻底废除,前后沿用时间长达数千年,就如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奏请删除刺字之刑时所说:“夫肉刑久废,而此法独存”⑴。自上古的五刑之一墨刑至清末的刺字之刑,虽然形式上毫无变化,但实质上却发生的很大的变化。在汉文废肉刑之前墨刑属于五刑之一,是封建国家刑罚制度中的正刑;在汉文帝废肉刑之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墨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废除,而成为国家刑罚制度之外的一种私刑,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和喜怒可以随意使用。到了五代后晋天福年间之后,墨刑又正式成为封建国家刑罚制度中的一种附加刑,直至清末被废除,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古五刑之一
墨刑乃是上古五刑之一,据《尚书》记载,墨刑起源于苗民,这可能与古代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文身的习俗有关⑵。《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姑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传:“黥面。”疏:“黥面即墨刑也。郑玄云,黥为羁黥人面。郑意黥面甚于墨额,孔意或亦然也。”《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劓。”《释文》:“天,剠也。马云,剠凿其额曰天。”《周礼》郑玄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额为疮,以墨窒疮孔,令变色也。”由此可见在上古墨刑就有黥额、黥面二种,黥面之罪重于黥额。
《尚书·吕刑》又云:“墨辟疑赦,其罚百鍰,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鍰,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鍰,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周礼·秋官·司寇》亦云:“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从上述记载可见,墨刑为五刑中最轻的一种,也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被大量运用于处罚各种轻微犯罪。如《周礼·秋官·司约》记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这是用墨刑来处罚虚假诉讼。
《汉书·五行志》云:“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这是用墨刑来处罚破坏环境的犯罪。李斯上书秦始皇,请求“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⑶”。这是用墨刑来制裁不遵“焚书令”的人士。商鞅变法,“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商鞅为了维护变法的严肃性,太子犯法,不能处罚太子,只能用墨刑处罚太子的老师。
近些年来地下考古发现的秦朝法律中也详细记载了以墨刑来惩罚各种轻微的犯罪,秦简《法律答问》曰:“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黥颜頯,畀主。”整理小组指出:,读为枯,《淮南子·原道》注:“犹病也。”并译为“私家奴婢笞打自己之子,子因此患病而死,应在额上和颧部刺墨,然后交还主人”。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秦朝的墨刑是黥额又黥面。奴婢笞打自己的儿子,儿子因此患病而死,仅处墨刑,如“擅杀子,黥为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子,勿罪”。如果擅自杀死自己的儿子,处以墨刑以后还要服“城旦舂”的劳役。但如果生下的新生儿发育不全或是怪胎杀死就可以不负刑事责任。
秦朝已开始在处罚盗窃罪中大量运用墨刑,秦简《法律答问》:“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黥⑺”。这是不得财的盗窃罪,处以黥刑,但可以金钱赎罪。得财的盗窃罪则根据得财的多少处以黥、劓、刖等不同的刑罚。秦简《法律答问》:“‘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求盗比此”。这是对五人以上共同盗窃,除了处以刖刑之外还要处以黥刑;不足五人共同盗窃,如果盗钱超过六百六十钱,除了处以劓刑之外还要处以黥刑,可见秦朝对群盗处罚之严。
汉承秦制,汉高祖入关,“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五刑⑨”。汉朝黥作为五刑中最轻的处罚运用亦十分广泛,汉律今已不传,但我们可以从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的汉简中窥知一二。张家山汉简《秦谳书》案例二十一:“夫生而自嫁,及取(娶)者,皆黥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娶)者毋罪⑩”。这是用黥刑禁止丈夫活着时妻子改嫁。张家山汉简《盗律》:“智(知)人为群盗而通(饮)食餽馈之,与同罪;弗智(知),黥为城旦舂。其能自捕若斩之,除其罪,有(又)赏如捕斩”。对不知为群盗为其提供饮食之人的处罚是黥为城旦春,明知为群盗而为其提供饮食的与群盗同罪。汉初淮南王黥布,原姓英,“咎繇之后,后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应相者之言”。可见汉初黥刑应用之广泛,受过黥刑的人之多。汉初黥墨之法甚至影响到其他少数民族的法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
除肉刑之后
汉文帝废肉刑的原因是汉文帝已认识到肉刑难以止奸,同时又堵塞了有罪之人改过自新之路,“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才决定用身体刑与劳役来代替肉刑,“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
至此黥、劓、刖三肉刑分别以身体刑与劳役来代替。汉文帝废肉刑除了黥刑之外,实际上是让受劓刑、刖刑之人死得更痛快些,与其求生不能,不如开辟一条求死之路,因此《汉书·刑法志》评论道:“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汉文帝废肉刑之后,黥、劓、刖三肉刑正式从国家制定的正刑中被删除了出去,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作为一种私刑还被保存着。《汉书·王莽传》记载:“初,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官,后又穿长安城,引内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张周帷,辑濯越歌。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于是上怒,以让车骑将军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谢太后。”
这则记载中成都侯商、曲阳侯根兄弟俩僭越之行被皇上发现后,自觉将会大祸临头,想要自己施行黥刑、劓刑之后到太后处请罪,说明这两种肉刑从正刑中被删除之后,作为私刑在某些特殊场合还保留着其合法的身份。《后汉书·蔡邕传》中有一条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书。
”这是蔡邕因同情董卓,王允要把他交廷尉治罪,蔡邕为了完成汉书,请求对自己处以黥首刖足私刑作为惩罚,以换取不交付廷尉治罪。上述两个事例至少说明自汉文帝废肉刑之后到汉末,黥刑作为一种私刑还被广泛运用着。《酉阳杂俎》卷八引晋令:“奴始亡,加铜青若墨,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对家奴逃亡被抓获以后处以私刑,以防止家奴再次逃亡,即使逃亡后也便于捕捉,这是突出了黥刑在防止罪犯逃亡中的特殊作用。
宋明帝时恢复了对遇赦后的盗犯使用黥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僄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僄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徒犹黥面,依旧补冶士”。梁武帝时“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黵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梁武帝继承了宋明帝的做法,但在天监十四年正月又下诏书曰:“世轻世重,随时约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犹念改悔,其路已壅,并可省除”,删除了黵面之刑。
但黥刑作为一种私刑却始终保存着,《北史·房谟传》:“谟悉心尽力,知无不为。前后赐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后赐其生口,多黥面为房字而付之。”神武帝害怕赐给房谟的奴婢均被他免放,所以在所赐奴婢的脸上刺上房字。由此可见,黥刑脱离了正刑后,作为私刑使用时反而比黥刑作为正刑时更可以随心所欲,丝毫也不用受到法律的制约。
入唐之后,黥刑作为一种私刑在宫廷内部或封建士大夫家庭内部仍被广泛使用。唐中宗时的上官昭容,名婉儿,是西台侍郎上官仪的孙女,幼时随母配入掖庭。“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则天时,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18]”。唐时黥面的私刑可能仅在额上黥一印记而已,所以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八中记载:“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点迹。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嫉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晚唐五代时,黥刑这一私刑被广泛运用于军队之中,这一做法的起因是为了防备士兵逃亡。“唐末士卒,疲于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旧五代史·朱汉宾传》中亦有记载:“梁祖之攻兖、郓也,朱瑾募骁勇数百人,黥双雁于其颊,立为‘雁子都’。梁祖闻之,亦选数百人,别为一军,号为‘落雁都’。”唐天祐年间,“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患之,多为僧以避之”。天祐三年七月,梁太祖朱温带兵攻打沧州,“乃酷法尽发部内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各自备兵粮以从军,闾里为之一空。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由是燕、蓟人民例多黥涅,或伏窜而免”。可见五代时黥刑用于强制征募来的士兵身上,以防备其中途逃跑,这一做法已是相当普遍,读书人为了逃避这种污辱,只能出家当和尚。
除了在军队士兵中广用黥刑以备逃亡之外,有时对怀疑其有异心的军队将领也用黥刑以防其变节。《新五代史·赵思绾传》记载:“景崇用思绾兵击走之。遂以思绾俱西,然以非己兵,惧思绾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随,而难言之,乃稍微风其旨。思绾厉声请先黥以率众,齐藏珍恶之,窃劝景崇杀思绾,景崇不听,与俱西。”
宋代的兵制亦承袭了晚唐五代的做法,在军队征募来的士兵中间广行黥面,以致于有黥兵之称。《宋史·兵志一》:“泰宁军节度使李从善部下及江南水军凡千三十九人,并黥面隶籍,以归化、归圣为额。”王安石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谓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王安石强烈反对对征募来的士兵用黥面的方法加以控制,主张对征募来的士兵与民兵同样对待。
其后,征募来的士兵不一定黥面,《宋史·兵志六》:“镇淮初,淮南募边民号镇淮军,数至十万,月给视效勇,唯不黥涅。”只有刺配充军者才黥面。
作为附加刑
黥刑作为正刑的附加刑最早起自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配之法,宋因其法,用重典戢奸,把黥刑作为徒流杖的附加刑,而重点用于处罚盗窃犯。“凡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典者黥其面。”“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黥刑作为附加刑,这时已有了轻重之分。初犯盗窃罪,在耳朵后刺环,判徒刑、流刑的在耳后刺方形,判杖刑的在耳后刺圆形;惯犯屡犯,处杖刑三次以上,刺字移到脸上。《庆元条法事类·刑狱门》对刺字大小根据刺配的远近都有不同的规定:“诸军移配而名额不同或降配者,所刺字不得过二分;逃亡及配本城四分,牢城五分,远恶及沙门岛七分。
即旧字不明及出除、遮盖者,官司验认添刺,不可添者,别刺。”这是把上古黥刑分刺额、刺面进一步细化,用附加刑所刺的不同部位和不同形状来体现窃盗罪的轻重,可谓用心良苦。开宝八年,诏:“岭南民犯窃盗,赃满五贯至十贯者,决杖、黥面、配役,十贯以上乃死。”宋初旧制,僮仆有犯盗主财,得私黥其面,太宗端拱二年诏曰:“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贯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这是规定用公黥来代替私黥,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淳熙八年,诏:“诸强盗贷命配军,于额上添刺‘强盗’字,仍差将校部送,余依本法。”
熙宁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贪赃枉法事发,法官判处张仲宣绞刑,援引前例从宽处理,杖脊,黥配海岛充军。知审院苏颂上疏:“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于是得免杖、黥,流贺州。其后,朝廷命官即使犯罪,也不必刺字。
北宋初年,《祥符编敕》中有关配隶的规定仅四十六条,宋仁宗庆历年间已增至一百七十余条。到了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又增至五百七十条,“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淳熙十四年,朝中臣僚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籍?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之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
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仿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牴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籍,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
南渡之后,已有不少人看到了滥施黥刺带来的消极作用,大声呼吁对稍轻和最轻的犯罪应免除黥刺之刑,用黥刺之刑专来对付那些情节严重的凶恶罪徒,这样才能为改悔之人开避一条自新之路。但是至宋末为止,这种滥施黥刺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就如沈家本在《刺字集序》中所说:“夫刺字亦国宪也,窃尝推原其旨,盖以凶蠹之徒,率多怙恶,特明著其罪状,俾不齿于齐民,冀其畏威而知耻,悔过而迁善。
其间或有逃亡,既可逐迹追捕,即日后别有干犯,诘究推问,亦易辨其等差。是所以启其愧心而戢其玩志者,意至深也。独是良民,偶罹法网,追悔已迟,一膺黥刺,终希望。身戮辱。”古人开设黥刑的出发点是驱恶迁善,但其施行的结果却是斩断了改恶从善之人的一线希望。
宋之后历代统治者已认识到“一膺黥刺,终身戮辱”这一结果对减少犯罪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从辽代开始对附加黥刑的罪犯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用所刺部位的不同来加以区别,给初犯者留下了一线改过自新的希望。辽统和二十九年,诏:“自今三犯窃盗者,黥额,徒三年;四则黥面,徒五年;至于五则处死。”兴宗重熙元年,“谕曰:‘犯罪而悔过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终身为辱,朕甚悯焉。’后犯终身徒者,止刺颈。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颈者听。
犯窃盗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颈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则处死。”辽统治者对刺面采取了一种较为慎重的态度,不轻易对罪犯黥面,正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面目一坏,谁复顾籍”的担忧。
进入法典
在宋朝黥刑作为附加刑是由朝廷的编敕所规定的,《宋刑统》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疏议》,所以在《宋刑统》中是看不到黥刑作为附加刑是如何运用的。元朝的法律今已不存,仅从保存在《元史·刑法志》中《大元通制》的某些法律条文来看,黥刑进入法典成为正刑的附加刑是从元朝开始的。
元初,仍沿袭了宋朝滥用黥刑的做法。“赦囚徒,黥其面。”但不久元朝统治者认识到滥用黥刑不利于减少犯罪,尤其对黥面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给犯罪之人留下一线生机。即使同样的盗窃犯根据情节轻重,有的处予黥刑,有的则予以免刺。《元史·刑法志二》:“诸窃盗,初犯刺左臂,谓已得财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刺项并充景迹人,官司以法拘检关防之。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因此蒙古人犯罪可以享有特权,免刺字。“诸审囚官强复自用,辄将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将已刺字,去之。”元朝的黥刑主要是作为窃盗罪的附加刑,窃盗罪主要以得财与不得财为轻重界限。“诸盗已到仓官粮而未离仓事觉者,以不得财论,免刺。”赃轻亦可以免刺,“诸窃盗,赃不满贯,断罪免刺。”但盗公物者从重处罚,“诸盗局院官物,虽赃不满贯,仍加等,杖七十七,刺字。”“诸盗守府文卷作故纸变卖者,杖七十七,同窃盗刺字。”
同样是偷盗粮食,“诸盗米粮,非因饥馑者,仍刺断。”“诸年饥。民穷,见物而盗,计赃断罪,免刺配及徵倍赃。”因饥荒被逼偷盗粮食,只计赃加倍追赃而免刺配,这是从犯罪动机上予以区别而决定是否附加黥刑。同样对窃盗案中未尽职守的有关责任人也予以免除黥刑,“诸工匠已关出库物料,成造及额余外,不曾还官,因盗出局者,断罪免刺。”
元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对盗窃牛马等牲口的犯罪比一般窃盗罪给予更严厉的处罚。元顺帝二年八月下诏:“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元代法律对擅自去除所刺之字以及刺字的部位都有详尽的规定,《元史·刑法志三》云:“诸为盗经刺,自除其字,再犯非理者,补刺。五年不再犯,已除籍者,不补刺;年末满者,仍补刺。”“诸应刺左右臂而臂有雕青者,随上下空歇之处刺之。
诸犯窃盗已经刺臂,却遍文其身复盖元刺,再犯窃盗,于手背刺之。诸累犯窃盗,左右项臂刺遍而再犯者,于项上空处刺之。”这一系列的规定可以说把黥刑这一附加刑的作用发挥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对明清如何运用黥刑来区分犯罪和减少犯罪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明初,朱元璋即帝位后,除了《大明律》与《大诰》规定之外,对黥刺等附加刑的使用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态度。《明史·太祖本纪》:“二十八年,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颁《律》与《大诰》,不许用黥刑、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在《御制大明律序》中重申:“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合黥刺者,除党逆家属并《律》该载外,其余有犯,俱不黥刑。”
《大明律》中刺字附加刑的运用也只限于强盗、窃盗两种犯罪,凡称与同罪者,止坐其罪,不在刺字之限。准盗论,免刺字,以盗论,刺字。即使是窃盗不得财免刺,得财者才予以刺字。《大明律·刑律》:“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但得财者,以一主为重,并赃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绞”。“凡盗贼曾经刺字者,俱发原籍,收充警迹。该徒者,役满充警。该流者,于流所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样者,杖六十,补刺。”同样的窃盗罪中,盗公物者刺字。“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等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
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盗官(钱粮物)三字。(注):每字各方一寸五分,每画各阔一分五厘,上不过肘,下不过腕,余条准此。”盗私物免刺,“凡各居亲属,相盗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并免刺。……其同居奴婢、雇工人,盗家长财物,及自相盗者,减凡盗罪一等,免刺”。”凡发掘培坟冢,见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盗取器物砖石者,计赃,准凡盗论,免刺。”妇人犯罪免刺,“其妇人犯罪应决杖,奸罪去衣受刑,余罪单衣决罚,皆免刺字。”而党逆家属该如何刺字,律无明文规定,这全由统治者的喜怒决定。如洪武年间,有“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左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
《大清律例》关于刺字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大明律》,有所不同之处即是增加了许多刺字的条例,因此比之明朝,清朝对刺字附加刑的使用范围又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清史稿·刑法志二》:“刺字,古肉刑之一,律第严于贼盗。其后条例滋多,刺缘坐,刺凶犯,刺逃军、逃流,刺外遣、改遣、改发。有刺事由者,有刺地方者,并有分刺满、汉文字者。初刺右臂,次刺右面、左面。大抵律多刺臂,例多刺面。若窃盗责充警迹,二三年无过,或缉获强盗二名以上,窃盗三名以上,例又准其起除刺字,复为良民。盖恶恶虽严,而亦未尝不予以自新之路焉。”
《大清律例》关于免刺的规定与《大明律》基本相同,但通过附增的条例对一些强盗,人命重犯被判死刑者增加了刺字的规定。《大清律例·贼盗下》:“条例:一、凡强盗、人命重犯、督抚审结,果系赃实盗确,并拒捕杀人窃盗,及律应斩决盗案,一面具题,即将面上刺‘强盗’二字,如内有监候待质者,于一边面上刺‘待质’二字。命案斩决等犯,亦即刺‘凶犯’二字。仍将已经刺字之处,本内声明,俟奉旨之日刺字监候。其戏杀、误杀、斗殴杀,俱免刺。直省等处如遇面刺‘强盗’、‘凶犯’、‘待质’等字样者,即擒拿送官。一、偷刨人参之犯,向例左右面刺字者,今改照窃盗例,初犯,刺右面;再犯,刺左面。”
从条例来看,对判斩决的死刑犯,在处决之前先行刺字,主要是预防他们在处决之前逃跑,如越狱逃跑后便于捉拿,但对已判处死刑的人来说命已不保,再增加刺字的附加刑对这些死刑犯已毫无意义。对偷刨人参的窃盗分为初犯与惯犯,分别刺面,对惩戒犯罪还有一定的意义。条例还对擅自销毁所刺之字和将功抵过分别予以奖惩,“凡窃盗等犯,有自行用药销毁面膊上所刺之字者,枷号三个月,杖一百,补刺。代毁之人,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凡窃盗刺字发落之后,责令充当巡警。如实能改过,缉盗数多者,准其起除刺字,复为良民。该地方官编入保甲,听其各谋生理[45]。”
从《大清律例》中新增补的条例来看,清朝刺字虽也分刺臂和刺面二种,但与明朝轻易不刺面相比,清朝的刺字附加刑有逐渐加重之势,所刺的范围也有逐渐扩大之势。这种沿续了数千年的以凌辱人格为手段的黥刑,到了清末光绪年间由于法律生存环境的变化,在中外人士的一致谴责和强烈呼吁下,才和凌迟、枭首、戮尸这些野蛮原始的刑罚一起被永远废除,真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原创文章,作者:来自网友投稿,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ladyww.cn/article/20230622155634.html